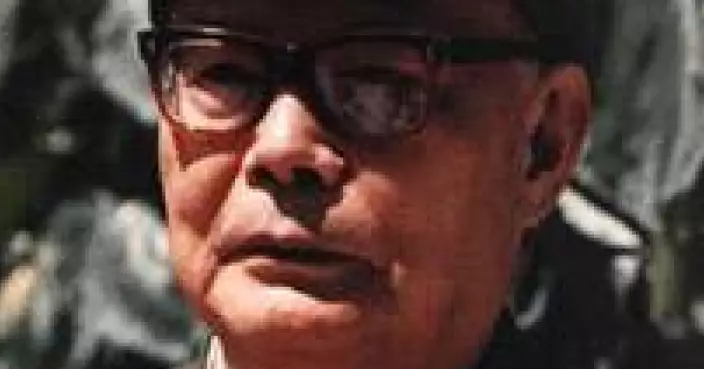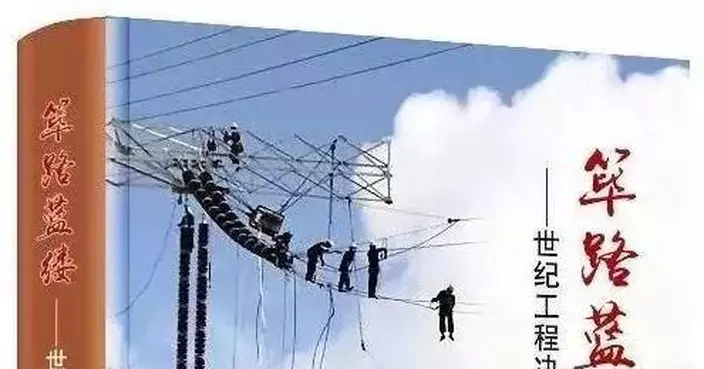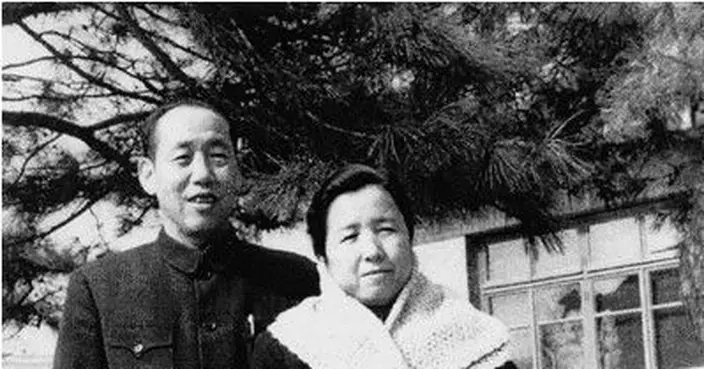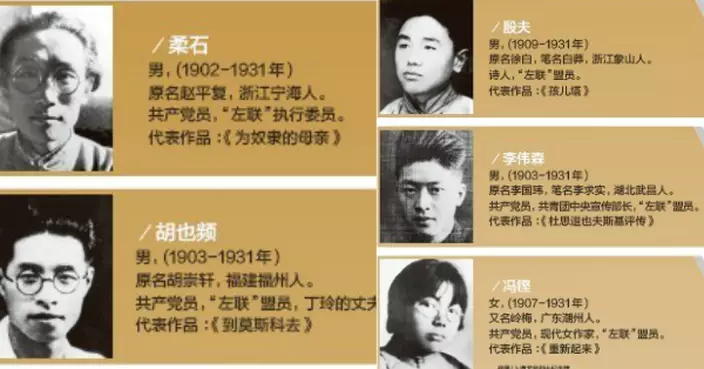1957年,鄧子恢陪同毛主席接見昔日閩西女紅軍戰士。

1966年8月,毛澤東與鄧子恢(左二)等在天安門城樓上,這也是倆人最後一次合影。
鄧子恢是新中國的農業專家,曾身居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他在農業問題上曾與毛澤東發生過矛盾,但兩個人是生死與共的老戰友,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閩西的革命歲月中就結下了牢不可破的戰鬥情誼。前不久,鄧子恢的兒子鄧淮生深情講述了父親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並稱這一直是父親引以為豪的一段歷史。
鄧子恢與毛澤東的初次見面頗費周折。
1929年3月,一直在閩西鬧革命的鄧子恢聞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從井岡山出發,經贛南殺向閩西、長汀時異常興奮,他深知紅四軍的到來將極大改變閩西的局面,便星夜趕往長汀會見毛澤東。還沒有趕到,紅四軍又撤離長汀向瑞金進發。鄧子恢知道紅軍神出鬼沒,於是寫信請求紅軍入閩,紅四軍決定重返閩西時,毛澤東也回信要求鄧子恢務必於5月22日在蛟洋見面。等鄧子恢到了蛟洋,紅軍因戰鬥需要又向龍岩推進,一心想見毛澤東的鄧子恢馬不停蹄又奔向龍岩,最後終於在龍門追上了紅四軍大部隊。紅軍官兵平等,憑肉眼很難辨認出誰是部隊的指揮員。經多次打聽,才見到了衣著簡樸,而威名遠揚的毛澤東、朱德。首次見面,舉止不凡的毛澤東給了鄧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毛澤東不再擔任紅四軍主要領導職務,他來到閩西休養,一蹲就是五個多月,特別是在蘇家坡的幾十個日日夜夜裏,鄧子恢與毛澤東交往甚密,朝夕相處,經常在一起探討馬列主義理論和根據地的建設等問題。鄧子恢為毛澤東傑出的軍事才能和獨到的見解所折服,視毛澤東為師長和益友,毛澤東也非常看重鄧子恢。那段時間裡,毛澤東不但處境不順,還患上惡性虐疾,身體腫得很厲害,十分虛弱。身為閩西特委書記的鄧子恢對身處逆境中的毛澤東非常關心,託人買來牛奶、白糖,每天燉牛肉湯、燉老母雞為其補充營養,並找來當地最好的醫生醫治。鄧子恢與毛澤東不以利交、不以勢交而是危難之中顯真情,這樣結下的戰鬥情誼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由於鄧子恢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毛澤東漸漸恢復了健康。不久,痊癒的毛澤東精神抖擻地重新走上了紅四軍領導崗位。1934年,毛澤東隨主力紅軍開始長征,鄧子恢留在了南方堅持鬥爭,兩個人不得不拱手告別,這一別就是12年,直到1946年倆人才在延安重逢,毛澤東高興地送給老朋友一張照片和一條毛毯。
鄧淮生告訴記者,父親對與毛主席的這段交往非常懷念,也特別引以為豪。即使後來受到了批評,甚到丟官賦閑,這段感情也沒有改變。鄧淮生手指一張合影告訴記者,這張照片是1966年8月在天安門城樓上拍攝的,也是父親與毛主席最後一次合影。
那天,鄧子恢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一次大型活動。活動間隙,他和陳雲在城樓上坐著休息。這時幾位老帥向在座的毛主席說:「我們想和主席照張相。」毛主席當即答應:「好啊。」老人家站起身,一眼看見了鄧子恢和陳雲,便招呼道:「兩位地方的同志也一塊來吧。」大家站好,攝影師按動快門,珍貴的歷史瞬間被永遠定格。回到家,鄧子恢難抑興奮的心情,把合影的事告訴了家人,言詞中流露著對毛主席的深情。
兩位老戰友在私人感情上沒的說,可在關鍵問題上都很「固執」,堅持自己的見解和主張,鬧得很不愉快。早在1955年年底,鄧子恢就因農業問題受到批評,但他不唯上,不唯權,無私無畏,敢於「頂撞」毛澤東。可是在家裏,鄧子恢從不向子女談及這些矛盾,特別注意組織原則,特別注意維護毛主席的形象。
鄧淮生平時長期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在那段不順心的日子裡,他常看到父親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靜靜地沉思,子女們都不敢上前打擾,一是怕打亂他的思路,二是不願意去觸及他的傷心事。鄧淮生所能做的就是陪父親下下棋,幫著散散心。不過有一次,鄧淮生實在憋不住了,大膽發問。
那是1962年夏季的一天,已考入哈軍工大學的鄧淮生因病在家休養。中央召開7000人大會後,開始對大躍進進行反思,在農業問題上要放寬政策。隨後開了廣州會議,中央定了農村60條,有些地方的農民允許有自留地,可以養雞了。1962年初,在有些省份出現了「責任田」。當時,《人民日報》上出現了對於「責任田」的爭論,有人說實行責任田好,能夠提高農民積極性;有人說不好,是單幹。老實講,鄧淮生當時只關注這些爭論的表面,還不能深刻的理解爭論的本質。一天,鄧子恢正巧在家,他知道父親在農業問題上有著精深的研究,也知道父親因農業問題挨了批評,以至於自己很長時間不敢觸及「農業」二字,這一回鄧淮生決定鼓起勇氣向父親發問:報上說的這些責任田、包產到戶都是什麼意思?出乎意料,鄧子恢聽後非常平靜,既沒有傷心也沒有沉默,更沒有抱怨、發牢騷,只是堅定地闡述了自己的主張,「包產到戶不是單幹,是農村經濟管理的一種形式,因為土地所有制沒變啊!好比工人計時做工和計件做工,單位時間內生產多少個零件。農民也一樣,一年內交多少糧食。工人做工可以包工包料,農民種地為何不能也採取這種辦法?」
這是鄧淮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向父親請教包產到戶的問題,父親的解釋雖不能讓他完全聽懂,但父親不隨波逐流、不說違心話,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忠貞不渝的高貴品德令其終生感佩。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