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會見溥儀合影(資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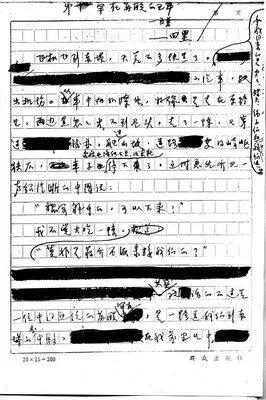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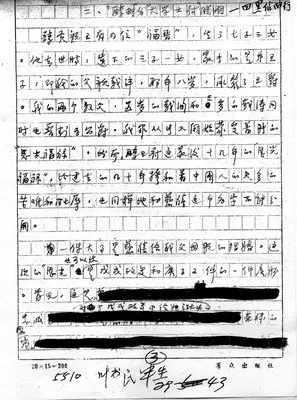
《我的前半生》手稿
一本國際公認的名著奇書,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擊,儘管它還是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認為「寫得不錯」的書。而認為它是“大毒草”的人,恰恰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階級兄弟,當然,也有在特定的“極左”時代精神迷亂者。歷史是斑斑點點的幾行陳跡,或許還能從中抽繹出一家出版社對這本國際公認的名著奇書作出突出貢獻的史實。
溥儀挨批評與困厄前的徵兆
1965年4月份,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申伯純找溥儀談話,轉達了周恩來總理對他的批評。溥儀被特赦到全國政協工作之後,總的來說,繼續改造得不錯,但也流露出一些自滿情緒。譬如,吹自己寫了《我的前半生》,在會見外賓等場合,未保持好謙虛謹慎的分寸,等等。周恩來總理說:「又為他出書,又常見外賓,不要飄飄然,飄飄然就要退步了。」“在撫順,進步。到政協,退步就不行!”周總理還給申伯純下了“命令”:“把溥儀交你,不能壞!”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日理萬機,一直代表著毛主席,十分關心對包括溥儀在內的獲釋戰犯的思想教育問題,嚴峻中飽含殷切的期望。
溥儀在自己的日記中檢討了自滿情緒(本文引用的某些史料,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愛新覺羅·溥儀日記》)。與《我的前半生》相關聯的是申伯純的一句對周總理的批評進行理解的話:「我揣度,出書事實上有別人幫助。」這個玄機,伴隨著與改革開放三十餘年同時的這本書的版權糾紛的發展,逐漸被公開且詳細化了。周恩來是智者,早在《我的前半生》問世一年之後,就把“又為他出書”的玄機道破了。這就使我想起了黑格爾所言,同一句話,由不同的人說出,其含義大不一樣。溥儀的“飄飄然”被有效地抑制,但周總理和溥儀離開塵寰之後,誰能抑制溥儀的夫人和某些族人的“飄飄然”呢?
周總理針對《我的前半生》的言論,是批評溥儀的一個角度。在20世紀60年代,還有針對這本書批評溥儀的其他角度。
《我的前半生》於1964年3月正式面世後,有一些讀者致函群眾出版社,批評這本書宣揚皇帝的顯貴,是「階級鬥爭的激烈表現」。較為典型的是偽滿時期溥儀的直接受害者、長春市政工程處職工孫博盛的批評。這位當年溥儀的“童僕”,表示對這本書的出版“抱著憤恨的心情”,並提出由群眾出版社做出檢討,否則要向中央寫信告狀。此事後來不了了之。群眾出版社妥善保管著這些信件,沒有告訴溥儀,以免給他平添緊張和不安。時間又過了兩年,孫博盛終於直接和溥儀“過招”了。
逆境中溥儀欲說還休
「文化大革命」初期,溥儀的腎病加重,口不離葯,經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樣,關心國家大事,對動亂歲月的一些反常情況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產生恐懼心理。他的歷史經歷又決定了他的恐懼以負罪心理為依託,久久不能釋懷。1966年9月15日,孫博盛以長春市政工程處文化革命戰鬥隊隊員的身份,致信溥儀,批評《我的前半生》的錯誤。溥儀於第二天複信,表示“書中內容確有不少美化舊事物,是不少有毒的,起壞作用的,應當打倒的”。還表示,作為危害中國人民的罪人,“不應當領稿費”。以此為開端,一直到翌年2月6日,孫博盛向溥儀致信8封,嚴辭斥責《我的前半生》,溥儀以及李淑賢給孫博盛回信9封,表示低頭認罪。真是難為溥儀了。實事求是地講,孫博盛討伐群眾出版社,是找對了單位;而興師於溥儀,則認錯了人。
話求救,據《愛新覺羅·溥儀日記》載,群眾出版社一姓張的人員,代李文達回話,說他工作忙。實際情況是,社方幹部張宗德把溥儀的求救推掉了,因為,造反組織掌了權,社已不社,李文達作為「走資派」早就被打倒而失去自由了。十分清楚當時的政治形勢的溥儀,又於10月21日與王蘭升電話聯繫,告訴孫博盛給他寫批判信一事。這應該是試探性的行為,還是想找李文達,也知道了王蘭升沒有出事。10月24日,溥儀給孫博盛複信,表示《我的前半生》以後不應當出版,“但是,這不是我個人能決定的,因此我已向群眾出版社同志提出了我的意見”……信中還極準確地揭示了《我的前半生》的主旨:“宣揚黨和毛主席改造政策的偉大。”似乎試圖扭轉孫博盛的思路。
「文化大革命」初期,溥儀的腎病加重,口不離葯,經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樣,關心國家大事,對動亂歲月的一些反常情況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產生恐懼心理。他的歷史經歷又決定了他的恐懼以負罪心理為依託,久久不能釋懷。
話向群眾出版社求救。他說:「我不是依靠李文達個人,而是依靠組織……自限於水平,再檢查,檢查不出什麼來……」他還表示,“政協領導對於書的來源不接頭”。溥儀就差說這本書不是他執筆寫的了。王蘭升不能跟溥儀說實話,只好講李文達出差了,而別人不知道書的內容。44年後,王蘭升告訴我,當時這樣講,是請示過造反組織的。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部都被砸爛了,哪還有什麼正經“組織”。
重災區在群眾出版社
群眾出版社至今完好保存著幾本厚厚的「文化大革命」檔案,其中許多內容頗具史料價值,而且是出版史研究的珍稀史料。因為是羅織罪名的誣衊不實之詞,引用起來有些為難,但倘不引用,看不清楚那個荒唐的年代,姑且全文引用一個段落,決無延續誣衊之意。
《我的前半生》這本黑書,是大特務李文達在地下黑公安部大叛徒徐子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復之和蘇特姚艮等人授意下,在大黨閥彭賊和大學閥陸定一和舊統戰部、舊政協的支持下,於1961年動手改寫,1964年正式出籠。
名義上是寫大戰犯、大賣國賊溥儀的勞動改造過程,實際上是配合帝修反反華、為劉鄧黑司令部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搞反革命政變大造輿論的。是一本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復辟宣言書。
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大叫這本反革命黑書「寫得不錯」,彭真也大叫大嚷“可以寫劇本”,反動學術權威黎澍,在一次黑會上更肉麻地吹捧說:“咱們私下裏說,這是一本不朽的書。”(黎澍所云「不朽」,是排除署名作者的。這是把握《我的前半生》的“書眼”——引者注)其主要罪行:
①大肆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妄圖為大賣國賊溥儀翻案。
②為大漢奸、大戰犯溥儀樹碑立傳。
③積極與大賣國賊溥儀及其反動家族、王公相勾結,惡毒地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
④陰謀炮製反革命影片《末代皇帝》。
李文達背著謝部長去找舊文化部走資派陳荒煤,在陳的支持下,決定由北影拍攝,由《早春二月》的黑導演謝鐵驪作導演,日本特務趙丹作演員。
⑤大肆鎮壓革命工農群眾給這本黑書提出的批評。
群眾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於1966年的夏天展開,第一個被打倒的是總編輯姚艮,不久之後,副總編輯李文達也被打倒。據王蘭升回憶,上述史料,大約產生於1967年上半年。姚艮和李文達在1967年上半年被投入監獄。這些文字不是面對面的批判材料,而是背靠背的批判材料,當時作為底稿,寫成大字報後,貼在公安部大院內食堂東邊臨時搭起的席棚上。
本文無意於探討「文化大革命」思維。這是一種在當時司空見慣且極少遭人質疑或批判的思維。筆者關註上述文字的出版史價值,約略說,有三條。
第一,它用簡短的語言,勾勒出《我的前半生》的成書過程以及為這本書的撰寫出版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最具悲劇意味的是少奇同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說過《我的前半生》「寫得不錯」的話,第一個說的是毛主席,但污水全潑到了少奇同志頭上。彭真是第一個提出要把《我的前半生》改編成劇本的人。陸定一為《我的前半生》的出版最後拍板。兼任群眾出版社社長的劉復之,在造反派當面聲討他的“罪行”時,坦然而明確地表態,《我的前半生》就是在我的支持和組織下具體完成的。在公安部,無論受迫害的老幹部,還是拉大旗作虎皮的造反派,沒有一個人認為這本書應該由溥儀來承擔責任。
第二,「文化大革命」耽誤了《我的前半生》用其他藝術途徑傳達的機會(以21世紀出版界的行話應稱為影視作品與圖書互動)。王蘭升回憶,李文達確實寫了這本書的電影劇本,他曾經看過。從當時的文化部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謝鐵驪到演員趙丹這條運作線索是真實的。世人只知改革開放以後,中意英合拍由尊龍出演溥儀的電影《末代皇帝》和國內由陳道明出演溥儀的電視連續劇,又有誰知道趙丹喪失了出演溥儀的機會呢?
第三,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第三研究所副所長黎澍、劉大年,都說過《我的前半生》「不朽」的話,並且得到了許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認同。在一本書尚未出版的撰寫過程中,就做出了這麼高的預期,在中國當代出版史上是不多見的現象,為我們今天根據歷史與邏輯以及政治策略,站在較高的位置上審讀書稿,提供了良好借鏡。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