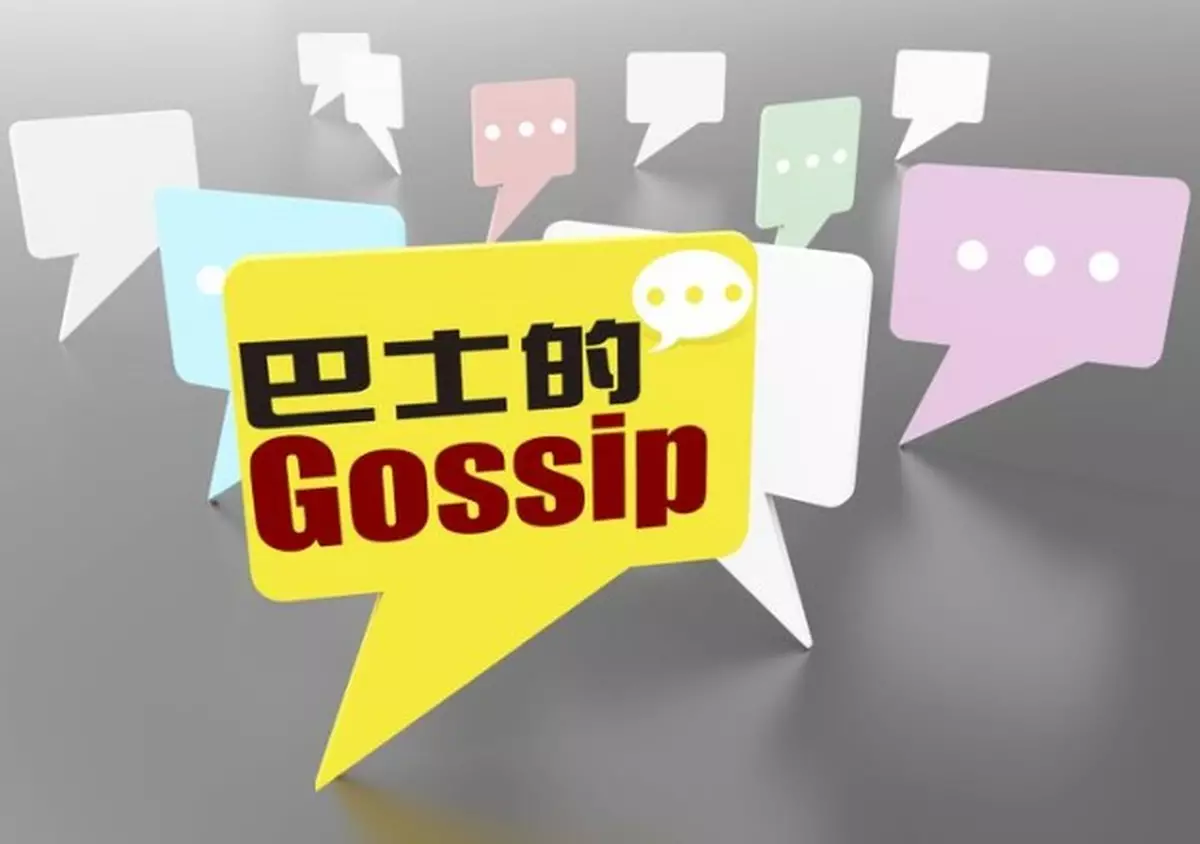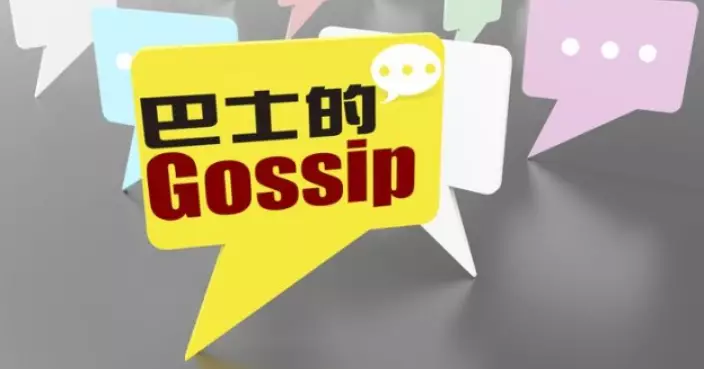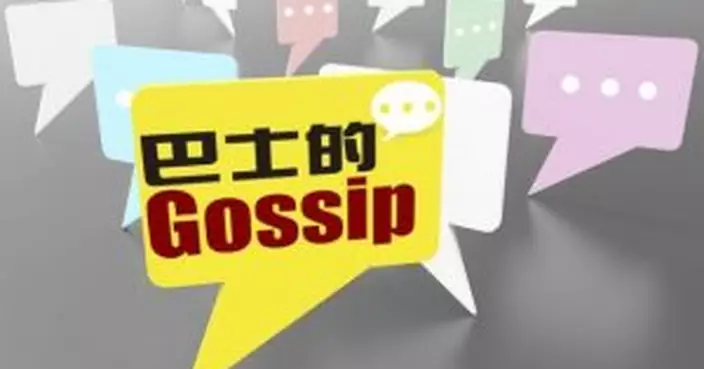在今日(7月1日)舉行的慶祝回歸28周年酒會上,特首李家超致辭時話,「常言道,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我們寧願做艱難的改革者,都不能做安逸的停滯者。現今地緣政治風雲變幻,不確定性不斷增加,香港可提供給世界的,正是安全和發展的確定性。憑著香港人的智慧和經驗,我有信心『東方之珠』一定能在世界舞台上,綻放更耀眼的光芒。」

特首超哥發言時引用清代文學家彭端淑的著名散文《為學》。
超哥引述的「天下事有難易乎?」的道理,來自清朝文學家、四川三大才子之一彭端淑的著名散文《為學》。
那幾句話的意思是:天下的事情有困難和容易區別嗎?只要付諸努力,困難的事情也變得容易;如果不努力實踐,容易的事情也變得困難。

清朝文學家彭端淑。
《為學》這篇文章完成於清高宗乾隆9年(1744)。彭端淑同族子侄很多,單單其祖父直系就有69人之眾,但當時連一個舉人都沒有,而彭端淑本人則是雍正年間進士。他見到族人的治學狀況,甚為憂心,急而訓之,於是為他們寫下這篇文章,用意是希望他們發揚嚴謹治學的風氣,勸勉子侄讀書求學不要受聰明愚魯的天資限制,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坐言起行。
《為學》一文著重論述做學問的道理,指出人的天賦才資並非決定學業有否成就的條件,只有通過主觀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先講為學的難與易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可相互轉化,轉化的條件在於人的主觀努力;平庸與聰明的關係也可轉化,如孔子的學說卻由天賦不高的學生曾參相傳,而不是由聰明的弟子傳承。接著講了四川邊境貧富兩僧想去南海的故事,富僧一直想僱船而不能實現,貧僧苦行一年而返,說明天下無難事,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點出立志為學這一中心命題。結尾指出,自恃聰明而不學者必敗,愚庸者能勤奮學習則必有成就。全篇採用以虛帶實,就實論虛的寫法,兩僧對比,觀點鮮明。
高人話,香港正值經濟轉型期,面對眾多困難和挑戰。香港也有很多聰明精英,喜歡坐而論道,對各種改革措施,諸多評彈,把自己當成一個評論員。但香港不用太多只講不做的評論員,要有更多落場踢波的行動者,他們不用太聰明,只要肯努力嘗試,在各行各業革新求變,香港必有所成。
若有興趣可看看《為學》全文: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與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于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缽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為學》白話文譯文:
天下的事情有困難和容易的區別嗎?只要肯做,那麼困難的事情也變得容易了;如果不做,那麼容易的事情也變得困難了。人們做學問有困難和容易的區別嗎?只要肯學,那麼困難的學問也變得容易了;如果不學,那麼容易的學問也變得困難了。
我的資質愚鈍,趕不上別人;我的才能平庸,趕不上別人。但是,天天學習,持之以恆,從不怠惰,直到學業有成,也就不知道自己原來的愚純與平庸了。我的資質聰明,高過別人一倍;我的才思敏捷,高過別人一倍。可是,丟棄不用,結果與愚鈍平庸的人相比,也就沒什麼兩樣了。孔子創立的儒家道統,最終由資質愚鈍的曾參承傳下來。由此可見,愚鈍和聰明,對一個人所起的作用,豈是一成不變的?
蜀地的邊境,有兩個僧人,一個貧窮,一個富有。貧窮的對富有的說:「我打算去南海,怎麼樣?」富者則問:「你憑靠什麼前往?」貧者回答:「一個水瓶、一個飯缽就足夠了。」富者說:「我多年來打算購買船隻沿江而下,至今還未去成。你究竟憑靠什麼前往!」過了明年,貧者從南海歸來,把這件事告訴給富者,富者流露出慚愧的顏色。西蜀離南海,不知有幾千里路程。富僧不能到達,貧僧能到達那裡。人們確立志向,反而不如蜀地邊境的貧窮僧人嗎?
因此聰明與敏捷,是可以依靠又不可以依靠的。自恃自己的聰明與敏捷的資質,卻不學習,是自甘失敗的人。愚鈍與平庸,是可以限定又不可以限定的。不受自己愚鈍與平庸的資質所限制,而是刻苦學習,不知疲倦,是力求上進的人。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