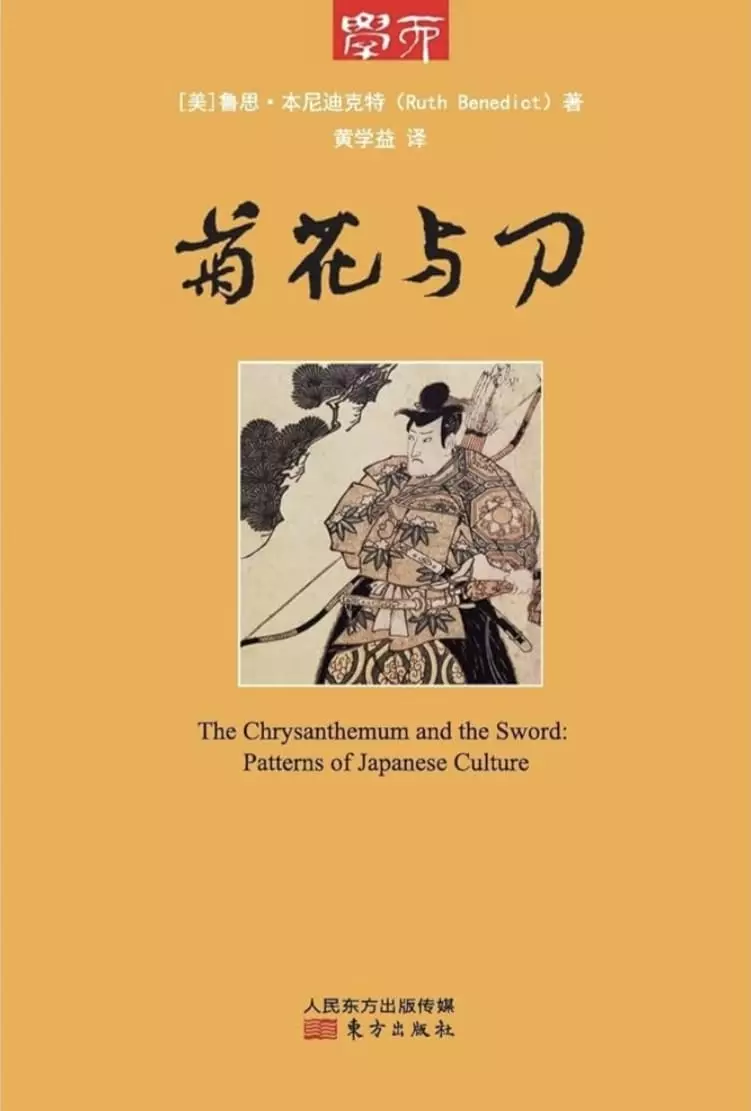最近和一個政黨老手聊天,他說4年前上一次立法會選舉的時候,很多人以為在新制度下,當選的議員就可以長期做下去,現在看來這顯然是一個錯判,新制度的特色是能者居之。
立法會選舉提名周四(11月6日)結束,總共有161人報名,較上次增加7人,來屆議會肯定會大換血。
第一、競爭激烈 淘汰性強
立法會有90個議席,來自選委會界別的黃元山在2022年底轉職政府特首政策組後,沒有補選,換屆前有89個議員,結果有54個議員參選競逐連任,但由於有3個議員出戰只有兩席的港島西直選(新民黨的陳家珮、民建聯的陳學鋒和工聯會的郭偉強3個現任議員同在這區參選,與自由黨的楊哲安和黃秋萍角逐),至少有一個現屆議員會在這區落敗,即是最多只有53個議員能夠連任。
換個角度,起碼有36個現屆議員離任,換血率至少40.4%,如果再有更多現任議員競選落敗,換血率會更高。在選舉前我估計換血率約30%,但結果是40%以上,換血比例比想像中高,淘汰性很強。亦預示新選制完全不如外界想像那樣,議員一當選就可以坐天下,可以一直做下去。
第二、新人湧現創新氣象
以下屆90個議席計,即最少有37個議席會由新人補上。先講地區直選,在10區共20個議席中,至少有6席,即30%,一定會由新人出任,包括新界東南和新界北兩個選區各兩席,現任議員全數不競逐連任,即4席會是新人。另外港島東及新界西南各有1名現屆議員不角逐連任,即兩區至少各有1個新丁當選。
在地區直選中,有大政黨背景的現任議員佔有優勢,如大黨取走一席,其他人要爭餘下的一個位,很多區都是4爭1的方式搶奪第2席,是一個爭崩頭的局面。部份地區大黨派出兩個候選人落場,更加會出現同黨互相𠝹票的狀況。
至於30席的功能組別,有45個新人參選,在28個功能界別中,有13個界別全數由新人出戰,例如法律界、工程界、建測規園界、社福界和旅遊界等,即是有43%席位一定由新人出任,換血比例更高。
至於選委會的40席,50個參選者中有24個現任議員,包括由其他界別轉跑道參選選委會的議員。即使假設所有現任議員都當選,這個界別至少有16人,即40%新丁入場。但以選委會的狀況,現任議員下馬的機會會比想像中高,所以新人的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鐵打衙門 流水議員
我們要透過每一次立法會的選舉,去了解這個新選制的特色。這樣高的換血率已經表明,「鐵打的衙門,流水的議員」, 沒有哪一個議員不可或缺,主要視乎他對整個體制有多大貢獻。
流亡海外的反對派主要攻擊本屆選舉很少有罵政府的人參選,他們似乎忘記了在4年前,他們還在攻擊那些參選人是「二五仔」,參加這個新選舉制度只是做花瓶。
其實要從有多少個罵政府的議員參選或當選的角度去衡量,這只是反對派的思維,他們以罵政府的聲浪來衡量體制的成敗,他們當然應該覺得美國的制度更加成功,因為在美國不單止在野反對派議員天天罵政府,在朝的執政總統也天天罵議員、罵傳媒、罵學界。特朗普罵反對的議員是國家的叛徒,罵媒體在造假新聞,罵學界是民主黨的傀儡。
我們的制度不是這樣,並不是用罵政府的聲浪高低來衡量體制的成敗,是要視乎新選出的議員,究竟有什麼真知灼見,有什麼高強能力,去推動政府,推動整個體制,推動香港發展向前。
盧永雄
日本這個國家的文化,表現出極致的兩面性----愛美而贖武,尚禮而好鬥,服從而不馴,喜新而頑固。這種雙重性格的惡劣一面,往往在中日關係體現出來。
內地《觀察者網》引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姚錦祥提到,日本民族「慕強心態」,認為「搞事早苗」們,總給人一種印象,日本只能被「打服」。
日本的「慕強心態」背後,有更深的社會文化根源。二次大戰末期,美國政府開始考慮打敗日本後如何在當地管治,特別是應否廢除日本天皇制度,於是委託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露絲.班尼狄(Ruth Benedict)做一個日本人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的研究,以協助制定戰後對日政策。露絲.班尼狄結果就在1946年出版了一本日本文化的名著《菊花與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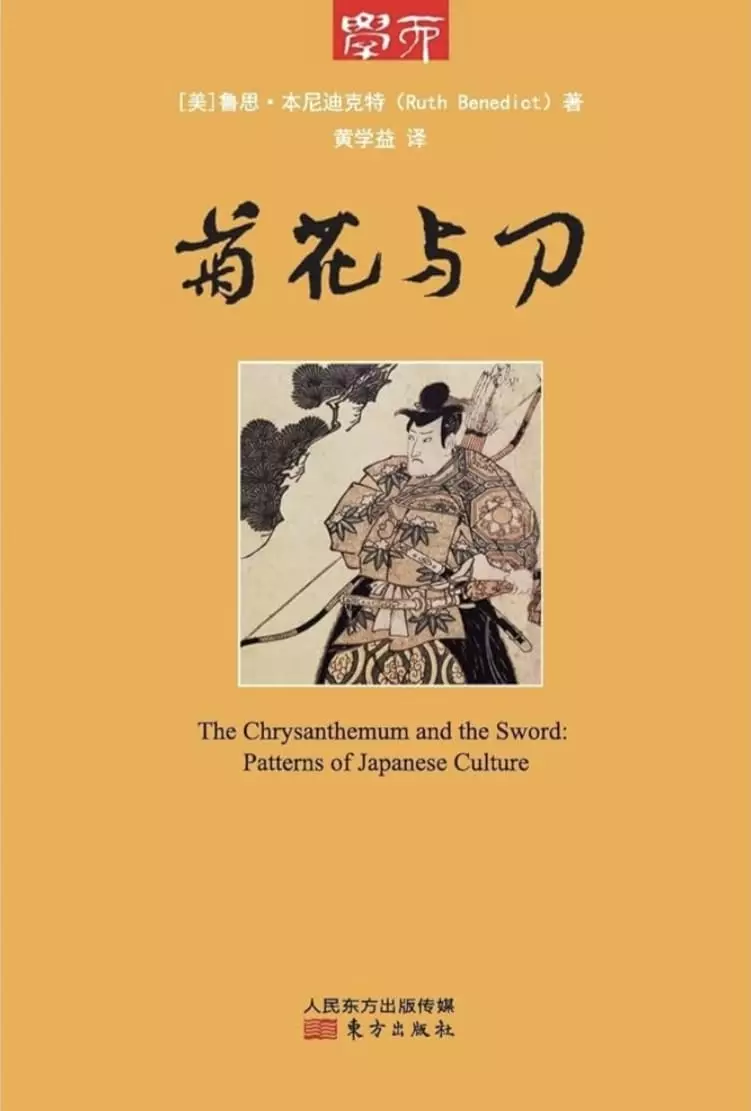
美國研究日本文化的名著《菊花與刀》。
菊花和刀就是日本文化的象徵,亦代表了其文化的雙重性。菊花代表日本文化中對美感、禮節和和諧的追求,體現在茶道、花道、庭院藝術等方面;刀象徵武士道精神,崇尚剛烈、尚武,甚至有為天皇犧牲的「玉碎」行為。
露絲.班尼狄很形象化地描述日本矛盾的文化。她認為,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日本是「恥感文化」,以外部評價規範行為;西方是「罪感文化」,以內在道德約束自己的行為。日本的恥感文化、天皇制度、階級分明,以忠於上級為義,以背叛上級為恥,對他人的恩惠要以忠誠回報。在看似矛盾的日本文化中,形成統一的體系。
雖然露絲.班尼狄的《菊花與刀》,被評為對日本文化的過份簡化、過份二元化的分析,但是其研究很形象化地點出日本文化的特質,亦影響了美國戰後對日本的政策。美國大量在日本駐軍,以軍事力量令日本人臣服;同時保留天皇制度,令日本人繼續臣服於天皇,而天皇臣服於美國。1945年9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親自去美國駐日本大使館,會見美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亞瑟將軍,拍下一張經典的照片。照片中,高大的麥克亞瑟身穿軍服便裝,雙手插袋,隨意站著。而裕仁天皇則身著燕尾禮服,站得筆挺。誰是主,誰是客,一目了然。美國成功逼令日本臣服於他的腳下,透過天皇輕鬆管治這個佔領國。

1945年9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親自去美國駐日本大使館,會面美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亞瑟將軍,拍下一張經典照片。
日本心理學先驅南博在他的代表作《日本人的心理學》中進一步解釋,日本的國家與個人都傾向在強大力量面前調整自我,順從強者,同時對弱者採取區隔態度。解釋了日本恥感文化下的慕強心態。
如今重讀露絲.班尼狄的《菊花與刀》,有深一層的現實意義。從《菊花與刀》的視角去看,日本在二戰後完全臣服於美國,並不是她價值觀的根本改變,而是她深層文化的模式面對外部劇烈變化的情景時,做出符合邏輯的調適。
日本人從一個戰敗的帝國體系,轉向一個由天皇《終戰詔書》背書、由美國主導的新體系。日本被美國打服了,也完全臣服於美國之下,這種驚人的轉變,恰恰體現了露絲.班尼狄所描述日本文化的核心特質,在固定行為的框架之內,有極強的情景適應能力。
當我們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對訪日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那種阿谀奉承的媚美神態,就知道日本對美國的臣服態度,雖然略顯誇張,但亦不足為奇。而與此同時,高市早苗妄言「中國如果改變台海現狀,日本就會出兵」,顯露出兇狠的反華態度,就知道她仍然視中國為弱者。日本對美國像是臣服的菊花,對中國郤亮出兇狠的軍刀。
還有日本評論者出來說,中國不應該以經濟威脅日本,但是他就不會評論特朗普單方面加日本15%關稅,並且逼令日本向美國投資5500億美元。
他們會將中國停止赴日旅遊和不買日本水產視為經濟脅逼,但是就不會視美國大幅增加他們關稅為經濟脅逼,主要因為他們內心臣服美國,而同時看低中國。
不過中國已非昔日的中國。中國面對這種日本文化,別無選擇,只能打到日本臣服,在外交上和經濟上令日本感覺到痛楚,那時日本她就會對中國產生「慕強心態」,那時日本就會明白,她只能用對美國的同樣態度,來面對中國。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