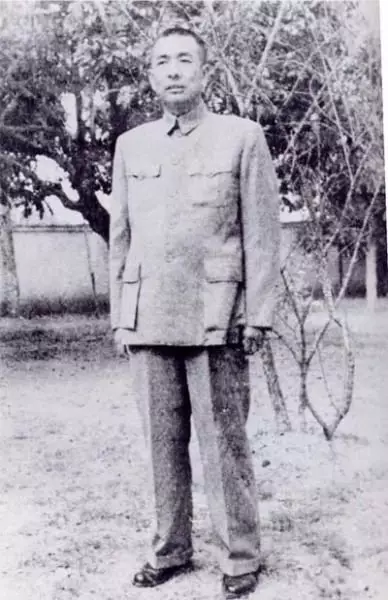
陶鑄(資料圖)
當6月1日陶鑄奉調進京時,曾先去湖南為韶山引水渠剪綵。就在剪綵儀式上,他曾深情地講話:「湖南是毛主席、劉主席,兩位主席的家鄉。」那時他不明白,「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指向了劉少奇、鄧小平;八屆十一中全會實際上是把劉、鄧“拉下馬”了,陶鑄卻仍然不相信,也不這樣看。陶鑄對妻子說:“他們只是犯了錯誤。劉少奇還是國家主席,鄧小平也還是政治局常委么。過去王明曾經犯了那麼嚴重的錯誤,紅區幾乎損失90%,白區幾乎損失100%,可是在延安七大毛主席還說服大家選他當中央委員。與王明錯誤相比,少奇、小平即便是有錯誤,也不會有那麼嚴重,還是團結、批評、團結。”
何止陶鑄這樣想,絕大多數中國人在1966年的下半年都是這麼想。就是說,陶鑄的想法在中國有深厚廣大的社會基礎、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甚至在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後,那些首當其衝地起來「造反」的紅衛兵們也並沒都聯想到劉、鄧身上。從“8·18”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到10月1日國慶節的盛大遊行,那些熱血沸騰的紅衛兵不是還在有節奏地高呼嗎?
「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那個時期的人們,一定還記得那大潮般的場面和聲音。儘管林彪已經躍居第二位,但紅衛兵要見毛主席時,首先想到的還是劉主席。這就是歷史的分量。
沒有劉少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國人民的解放史、中國革命的歷史甚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都將出現巨大的空白。這個空白是任何其他人其他辦法所無法填補的。
這也是歷史的嚴酷無情。它是不以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國慶節,毛澤東第四次檢閱了百萬紅衛兵大軍及革命師生,工農兵代表。盛會之後,新華社有關負責同志都到陶鑄這裏請示:「今年國慶的新聞照片如何見報?」依照慣例,新華社每年國慶之後都要發一組新聞照片。過去中央有規定:其中必須有毛主席和劉主席兩人在一起的一張。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形勢明顯有變,這次怎麼辦?陶鑄略作沉吟,拍板決定:“按過去的規定辦!”
見報是件大事。陶鑄對準備見報的一組照片進行慎重審查,並馬上發現了問題:「怎麼沒有小平同志的鏡頭?」陶鑄問。
新華社的同志互相望望,猶豫道:「沒有合適的。」“怎麼回事?”陶鑄立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自從大搞“三面紅旗”之後,毛澤東便多次抱怨“鄧小平耳朵聾”,可是一開會就“躲”他很遠。看來,這位倔犟的總書記,即使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被“拉下馬”後,仍然是這樣。新華社的同志報告:“我們選過了,沒有拍照上。”
這可真棘手了。陶鑄深明現在這種「非常時期」報紙的重要性。多數大轟大嗡大吵大鬧的造反派對這場運動本來就具有很大盲目性,何況當時還存在一些政治投機者,任何一次大的政治活動,哪些人見報了哪些人沒見報就成了他們十二分關注的事情,他們就是從這裏嗅查“問題”,從而決定其行動的。“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嗎?”陶鑄問。
新華社的同志說:「可以做技術性處理。」陶鑄再一次拍板定案:“可以這麼辦。”於是,毛主席和劉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見報了。於是,新華社的同志將一幀照片上的陳毅隱去,將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補過來,也見報了。這樣做決不是要損害陳毅同志。因為陳毅同志還有其他照片可以上。這就是後來鬨動一時,被江青大肆渲染的所謂“換頭術”事件。按照我們黨的傳統,主席夫人是不能與主席並列檢閱的。按著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較邊遠的地方。這也是陶鑄的決定:“按照規定辦。”那時有句叫得很響亮的話:槍杆子,筆杆子,革命靠這兩杆子。陶鑄在“筆杆子”問題上所作這一番決定,毫不奇怪地得到了“反作用”。國慶節後,他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回到家裏坐下歇息的時候,總是用手指無意識地在沙發上划來划去;或者背著手,低著頭在室內很不安地踱來踱去;眼神沉鬱,面色灰黯。這種心事重重的神態引起曾志的關注。
「出了什麼事了?」曾志小聲問。陶鑄不吭聲,只是一個勁踱步。“到底出什麼事了嘛?”曾志忍不住提高一些聲音。“沒什麼!”陶鑄只扔下這麼一句。
曾志被噎得憋住一口氣半天吐不出。她對丈夫最大的意見就在這裏,哪怕把她當作一名普通的同志呢,也該交流一下思想,何況這一次是丈夫主動希望她留下來作「內助」呢。
不過,曾志很快就想通了,丈夫這種態度不能只看作「大男子主義」,其實這正是組織紀律性強的表現。對於自己所主管的工作,決不對外人亂說,哪怕是對自己的妻子。
曾志開始留意觀察周圍的事物,很快便發現,康生的老婆曹軼歐已被派到陶鑄這裏來協助工作,而陳伯達的老婆也被分配到陶鑄所主管的工作部門中來。
毫無疑問,陶鑄已經成為不可信任的人。他與中央文革已陷入很深的危機中。
終於,陶鑄也有憋不住的一天。他在急促的踱步中,從齒縫間漏出四個字:「這個婆娘!」
只有四個字,卻足以使曾志驚心動魂。只有曾志明白這四個字的分量和意義。因為在廣州,陶鑄便經常把江青稱為「婆娘」,而且聲音很大。只要江青不在場,他從不忌諱其他人聽了會怎麼樣。
他已經和江青對立起來,江青可不是當年去廣州「養病」的婆娘了,她已經被標上了“旗手”。
陶鑄走進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一眼就看見了他最不願意看見的江青。不見是不可能的,這是中央文革碰頭會,他是文革小組的顧問。陶鑄的眉毛本能地抽縮了一下,他的弱點就是不善於掩飾感情,缺少城府。大概他也有自知之明,忙轉身關門,避開江青的目光,順勢右拐入座。可是,江青頤指氣使的尖聲已經追過來:「你們看報紙了嗎?這些照片發得是很有講究的,我找了半天也認不出哪個是我。」
江青發難了,她被排得「邊遠」了。陶鑄坐下時,已然竭力剋制了情緒。他平靜地望住周恩來,建議:“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不如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聯繫工作或是參加活動也有個名義。”
「你們碰到鬼了!」江青叫起來,那聲音帶著穿透力直衝陶鑄耳膜。他忍住沒有回頭,但可以想像到江青盛怒的面孔。他聽到江青拍了沙發扶手:“我怎麼能作這種事情!”
廳里有那麼片刻如啞了一般靜。陶鑄的建議無疑是在提醒江青自重,也是對國慶照片的人員排列作出回答,表明這裏存在著原則性。而江青的尖叫無疑表明陶鑄簡直是在污辱她。她自認為主席夫人、文革小組副組長,憑這兩條就該列入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了。
碰頭會進門就來勢不妙,那結果便可想而知。剛宣佈會議開始,江青便首先發難了。
「陶鑄,」江青直呼其名,矜持得連二郎腿都不曾放下來,以此提醒陶鑄明白明白她是處於什麼地位,那完全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質問口氣:“你為什麼遲遲不去宣佈吳傳啟為革命左派?”
陶鑄是烈性子,聽到直呼其名的聲音尖厲,口氣兇惡,說話蠻橫無禮,
差點跳起來。只因為及時接到一個信號才忍住了。那信號就是周恩來的目光。可是陶鑄還是以眼還眼地望住了江青。他的眼睛閃爍一下,迅即又變得漆黑,腮上突起了肉棱,微微作抖的身體預示著一觸即發。
那一刻,整個河北廳都凝固了。挑戰者和應戰者劍拔弩張地對峙著。
江青很賞識兩個人:教育部寫第一張大字報的盧正義和學部寫第一張大字報的吳傳啟,一再催促陶鑄去教育部和學部,封他們兩人為「革命左派」。陶鑄掌握了很多確鑿的事實和材料,證明這兩個人都是有重大歷史問題的心懷叵測的人。為此,他再三向江青說明事實情況,表示不能封他們為「革命左派」。可是江青哪裏肯聽?只顧堅持催逼。
後來,在盧正義問題上陶鑄作了些讓步。他去教育部講了一次話,對盧正義的大字報表示支持,但是對盧正義的歷史問題,仍然表示要放到運動後期處理,並且沒有按江青意圖封盧正義當什麼「左派」。
至於吳傳啟,陶鑄始終堅持一步不讓。
在周恩來的目光暗示下,陶鑄鬆開緊咬的牙齒,低頭喝了兩口茶水,算是主動緩和了氣氛,然後掀起眼帘,換上較溫和的目光重新望著江青,竭力用一種平和的語氣說:「吳傳啟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他的材料你已經看過?」“我看過了!”江青自我感覺贏了一個回合,口氣更硬。陶鑄皺起眉頭問:“既然看過,我怎麼能去支持這樣一個人呢?”陶鑄的態度已經有所退讓。與過去相處比較,他對江青這樣講話已是很禮貌很客氣。但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感覺,從來不是靠語言,而是靠無所不在的直覺。直覺可以從眼睛的一瞥,肌肉的一顫體會到那微妙的所在。何況,陶鑄在炮打劉鄧還是保劉鄧的問題上,在派工作組和「文化革命」的搞法上,都與中央文革、與江青的觀點大相逕庭。江青不識大局,不識大體,只憑個人好惡走極端。小肚雞腸又鼠目寸光;肚裏容不得人,眼裏放不下事。比如對陶鑄,感情好時,看他是男性十足的男人,說什麼都好接受。感情不好了,便看他是惡意十足的惡人,一無是處,一句話也聽不進去。“只要是寫第一張大字報的,就必須承認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須支持他們!”江青完全是用教訓和命令的口氣講話。“不問動機目的,不問政治歷史背景?”陶鑄幾乎想質問:是不是蔣介石在台灣寫了第一張大字報的話,你江青也要支持也要封他為革命左派?但在這種會議上,陶鑄不會這樣說。他只是搖搖頭:“我不能不問動機,不看歷史。”
「至於歷史問題么,那有什麼了不起!」江青嘴唇開咧成喇叭形,鼻子兩側出現挖苦的紋絡:“你不也是國民黨嗎?”
現在說個國民黨似乎問題不太大,對外開放了。那時不得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鬥爭的繼續”,你站哪一邊?
陶鑄猛地瞪起眼,紅紅的,像打開了火山口。他本來嗓門大,這時的吼聲更加火山噴發一般隆隆震耳:
「你知道我是什麼時候的國民黨員?我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員,是在國民黨軍隊集體參加國民黨的!那時毛主席也是國民黨!周總理也是國民黨!還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黨第一軍的黨代表!他們都是我的頂頭上司,我只是國民黨的一個小兵!還想怎麼著!你先讀讀歷史去!而吳傳啟是什麼性質的國民黨員?他的國民黨員能夠與我們的國民黨員混為一談嗎?」
陶鑄吼罷,山搖地動地啐了口痰。
「文化革命」期間,政治局會議,文革碰頭會以及中央處理各省市自治區問題的接見會,都發生過不少爭吵,甚至是驚心動魄的“大吵大鬧”。比如後來發生的所謂“二月逆流”;比如處理青海、雲南等省的問題。但是跟江青真刀真槍面對面地大吼大叫,許多工作人員都說,陶鑄是第一個。
他沒朝劉鄧開頭炮,卻朝江青開了頭炮。
江青最初被吼惜了;臉色煞白,兩頰的肌膚都鬆鬆地垂下去,嘴唇開剛著微微顫抖。她當上「第一夫人」後,哪裏遇到過敢如此“放肆”吼她的共產黨幹部?轉瞬間,她的嘴唇繃緊,一股血衝上頭來,臉孔甚至頭髮根都漲得紫紅。她眼裏冒出火,那是狹隘刻毒女人常會冒出的怨憤之火;她嘴角兩側朝下氣勢洶洶地延伸出兩道深紋,你若聽聽現在工作人員的形容立刻可以想到後來江青受審時的一幅照片,就是那照片上的形象。但她那時不是依在被告席的鐵欄上,而是坐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的沙發里,並且奮力拍打一下沙發扶手,銳利地叫喊道:
「你給我去,到學部去,去支持吳傳啟,你非去不可!」“我就不去!”江青的手還沒從沙發扶手上縮回,陶鑄的大巴掌已經緊追其後拍在了茶几上,並且跳起身。他一輩子英雄主義,也從沒遇過敢這樣喝斥命令他的人。於是腦袋像穿甲彈,硬梆梆地挺出去:“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寬了。”
他感覺有人拉他,但盛怒之下哪裏肯退讓?怒目圓睜地繼續吼:「這是共產黨的組織,你什麼事情都要干涉!」
陶鑄被拉著坐下,那邊的江青卻痴痴地睜著眼,不知所措;上下牙床拉開距離,半晌合不攏。
突然,她哭了。不少文章都寫過江青哭,一寫就是「大哭大叫」,其實簡單化了。
她的哭很複雜。最初是從積滿怨毒之氣的胸腔里迸出一股短促的氣流,像是憋不住而衝突出來,馬上被哽住。這短促突兀的怨氣直衝鼻腔,多數從鼻孔里衝出,極少數從嘴裏溢出,將嘴唇激得「啵」一聲抖;只這一聲,眼裏便濺出淚來,沒有淚水充溢眼圈再決堤而出的過程;淚水是被怨毒之氣驅趕著從淚腺直接濺出眼眶,落在眼瞼下兩滴,像掉落下的兩顆雨點。
然後,眼圈才開始循著規律充血變紅,大量的淚水才滔滔不絕地湧出。可也沒有馬上吼叫,而是先掏手絹。
康生無動於衷地坐著,甚至眼睛也眯起來,目光從眼縫裏閃出,輪替在江青和陶鑄身上稍觸即離,頻觸頻離。張春橋也坐著不動,冷冷盯緊陶鑄,目光陰森,一邊用手輕觸江青的手臂。陳伯達和姚文元早已跳將起來,本能地靠近江青,保駕一般。一邊指著陶鑄吼叫,一邊對江青俯耳勸說。
只是到了這時,江青才開始口頭出聲,喊出聲,並且像某些色厲內荏的孩童一樣,越勸越起勁,越勸越聲大,成為真正的大哭大叫:
「我這一輩子還沒受過這麼大氣!你陶鑄想幹什麼?想壓迫我?你給我說明白!啊,你欺侮我,你鎮壓我,你算什麼東西?你到底想幹什麼?」
事情鬧到這步田地,周恩來明智地宣佈散會。陶鑄起身就走,身後還響著江青的哭叫。
唉,躲了今天躲不過明天。陶鑄臉色陰沉地登上汽車。據警衛曾雲同志回憶:
「從文革碰頭會出來,他心情沉重,眼裏潮濕,上車時自言自語說了一句:讓她這麼個搞法,以後怎麼得了?當時我知道江青他們中央文革那幫人鬧得凶,打倒幹部太多。每次碰頭會都是在河北廳,他們在裏面吵,我們一大幫警衛在廳外等候,聊天,我們不談政治,這條大家心裏都有數,只談地方特色和生活。那天陶鑄是第一個出來,走得很快,一路無語,只到上車才自言自語地說了那麼一句。」
第二天,陶鑄又接到通知,參加文革碰頭會。汽車駛向人民大會堂時,陶鑄仰靠坐椅,以手加額:剛吵過,今天還怎麼碰頭啊?
本文《紅牆紀事》,李健著,中國言實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